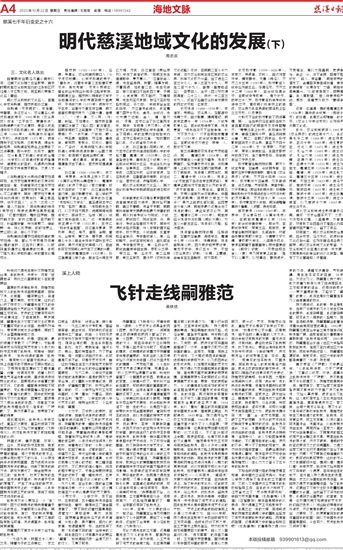听说过之佛先生有长女陈雅范在台湾,做乱针绣,去年十一月有“甘霖世泽”陈氏三代画展赴故乡在故居展出。
画展的热点是乱针绣,陈雅范和她女儿的乱针绣作品琳琅画廊。但除了绣,也有画。一幅写意山水,岛渚之上,暮云寒林,宋元笔意,让我们认识了陈家女公子嗣雪先生不凡的中国画造诣和大气的山水笔墨精神。数幅工笔花鸟,家传的工笔兼写花鸟功夫深厚纯正,不但有其形,更传其神。嗣雪先生次女蔡文恂女士还带来了数量可观的水彩作品,色调热烈缤纷,带来更多域外多姿情味,同时又不乏含蓄典雅亲和之作。
对于乱针绣,我是一团乱麻。最初读高尔泰散文《广陵散》,才晓得早年苏州丹阳正则艺专有个小老太叫杨守玉发明了乱针绣,那是谜一样的乱针绣。“她所创造的画种‘乱针绣’,是用针线代替画笔和色彩,在布上作画无数不同色彩不同长短的丝线,不规则地相互横斜交叉错综重叠,近看一片混沌无序,远看人物风景生气洋溢光影迷离,画法有点像印象派的点彩,但要用点彩法临摹它根本不行。它的每一幅都是独特和不可重复的,无论是深巷里墙头落日的余晖,灯影暗处的裸女,雨中的树或者阳光下灼灼生辉的一团黄花,都像是不久就会消逝的东西。”作者在文中把乱针绣错当作无人继承的“广陵散”了,虽然于事不合,却更有了叙事的诗意。
但孤陋如我,乱针绣从未尝见过。直至这次展览,直至我读到了陈雅范和她女儿文怡文恂编著的《飞针走线》,我对乱针绣才有了感性和理性的认识。
民国初年,精于西画,亦写人物、山水、花鸟的杨守玉教授,有感于中国刺绣针法过于呆板,她将西画素描的基础,用之于刺绣的技术上,主要采用长短交叉的线条,以分层加色手法来表现画面。西方透视法与中国刺绣针法的融合,创新了刺绣的新方法,研究发展成了一种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乱针绣”,改变了刺绣的生命。在绣法通于画法、针法通于笔法的原理下,产生了综合性的新艺术,是中国刺绣史上的一大革新,从此中国刺绣突破工艺的樊笼,走向了纯粹艺术创作的途径。
乱针绣为什么要加上一个“乱”字呢?因为这种刺绣的特色是着重于线条的变化,乍看起来线条很乱,其实乱中有序,有它一定的针法原理,或粗或细,或长或短,纵横交叉堆砌皆有脉络可循,绣法通画法,乱中皆有其道理。
陈嗣雪扔下美术十多年之后才拾起乱针绣。
“一九四九年(民国三十八年)三月,随着外子的工作单位,一家三口乘坐‘海张轮’迁来台湾,离乡背井……一九五二年外子考取第一届留美军官,前往受训,那时候我们住在南港兵工厂宿舍。我由一个无忧无虑的家中娇女转变为相夫教女的家庭主妇。刚到台湾初期,生活条件相当差,做饭,洗衣,剪裁车缝,编织毛衣,剃头,整修房屋油漆,为了节省开销,每一件都必须自己动手,也可算是双手万能,只是于艺术无缘。唯一让我纾解生活压力没有和艺术脱节的,便是偶尔去台北的中山堂看看书画展览。一九六二年,父亲突然在南京过世的消息辗转从香港的朋友处传来台湾,这个噩耗令我悲痛欲绝,同时像一记重锤打醒了我。我开始思念着父亲的一切,父亲开始专攻工笔花鸟画时,以号‘雪翁’为署名,而我的本名叫‘雅范’,父亲在我进入中大艺术系时,特别给我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嗣雪’。”
一个女子,忍受丧父的悲恸,在海峡彼岸,抑制无法奔丧的遗恨,开始着手进行疏离了十几年的艺术创作。陈嗣雪绣的第一幅乱针绣作品是《和平的障碍》,挨着铁丝网张望的两只和平鸽,带着暗色调的凄楚和哽咽。接着她开始尝试绣人像,“是亲情的感召吧,从来没学过如何绣人物的我,凭着身边仅存的一小张父亲的照片,拉回了鲜活、浓郁的回忆,心中惶恐之至,完成后我请父亲的高足傅狷夫兄批评,他说神态逼真,也许这就是父女连心的缘故。第二幅作品的成功,不仅使我的信心增长,创作的胆子更壮大了,于是各种题材便在灵活的运针下一幅一幅地完成,五年里完成了以作品纪念父亲的心愿。”一九六七年,在台北新公园的省立博物馆举行第一次个人绘绣展。这个博物馆在六十年代是最好的艺文展场。一个弱女子,一个奇女子,足不出户,五年时间,五十幅乱针绣作品在眷村诞生。眷村,南港兵工厂宿舍里沸腾了,“想不到我们眷村里真是卧虎藏龙!”展览结束,虽然一炮而红,回想筹备展出所经历的点点滴滴,令她心酸,虽然喜悦,但内心的哀痛,却渴望痛哭一场,当时她写了一封“永远寄不到的信”给亲爱的父亲,向他告白女儿没有辜负他的赐名“嗣雪”。她觉得自己像一盏熄灭已久的灯火,又亮了起来。
陈嗣雪在《飞针走线》开篇中就说:“造就一个艺术家必须具备的两个因素,先天的与后天的……何其有幸上苍很慷慨地把两个都给了我。”第一个因素,不说了,因为她是陈之佛的女儿,而且母亲的女红也特别好。于是从血缘深处升起了一股自豪的情感,这种情感的觉醒对于陈嗣雪来说是很重要的。她此后的人生态度中始终没有失去中国人已化为血缘形式的情操——气节和风骨。从小生长在艺术气息浓厚的环境,耳濡目染,“我从三岁开始便喜欢涂鸦,听说我曾画了一个椭圆形的东西,就是爸爸的茶壶,父亲高兴极了,夸我长大后能当画家,那时候我画的童画都被父亲收集起来,后来他编写儿童绘画书籍时还用了上去。从有点懂得看画开始,父亲常让我当他的小跟班,随着他参观各种艺术展览。我会和乱针绣结下一世一生的缘分,也是因为在父亲带我去参观全国美展时,看到杨守玉的创作,她以绣作画的特殊艺术表现,深植我心,但那时我只有十一二岁。抗战爆发,翌年一月辗转到重庆,去吕凤子创办的正则绘绣专科学校学画,跟我向往已久的杨守玉老师学乱针绣。乱针绣是一种绘画与刺绣息息相关的艺术创作,为了打好绘画基础,我又转到中央大学艺术系,第一年以理论课与素描为基础。第二年由于我偏好石涛的山水与父亲的工笔花鸟,选修了中画组。”陈嗣雪坦率地说,教授山水的黄君璧和教授花鸟的谢稚柳并未对她的学画历程造成深刻影响,她很幸运在家中可学到更多、更仔细的技法,她既是之佛先生的小跟班,又是小书童,磨墨也好,换水也罢,在画桌边伺候的时候,可以仔细地观察父亲如何用笔、用色。父亲常叮咛说,“色要艳而不俗,淡而有情,工笔画更是美在线条,须柔而有力。”这些话陈嗣雪记了一辈子,后来都运用到了乱针绣上。
1991年,在第一次个展的四分之一世纪后,陈嗣雪在台湾历史博物馆举办了七十回顾展,展出了七十幅新作,还出版了台湾第一本介绍乱针绣的《飞针走线》。
无论之佛先生的工笔画,还是嗣雪先生及女儿的乱针绣,都推陈出新,中体为本,洋为中用,从工艺走向了纯艺术的尚美之路,也正是陈嗣雪与其父的共通之处。“雪个已矣瓯香死,三百年来或在斯。”陈之佛那清新隽逸、雍容典雅的独创风格,远绍徐黄,直登宋元堂奥,并受明代吕纪、清代恽南田的影响,既博采众长,又独树一帜,把传统的花鸟画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他善于汲取历代花鸟画的精华,在用笔、用墨、用色上极为讲究。又大胆运用西洋的解剖、透视等科学表现方法,以及构图色彩的形式法则,以加强花鸟画的艺术效果。陈之佛认为花鸟画和其他的画种一样,首先要求画家有健康的思想感情,在提高思想水平的同时还必须注意提高艺术水准,要有一定的表现能力,个人的精神体验和深刻的感受才能在相当娴熟的笔墨形式中体现出来。他的作品,既没有院体柔媚拘谨,也不受文人画狂怪的影响,却蕴其抱朴含真旷逸空灵之美。1934年,他以“雪翁”署名的花鸟画在南京中国美术会第一届美展上展出,引起轰动。1935年后,陈之佛开始专攻工笔花鸟画。1942年3月1日,又在重庆首次举办了个人作品展。“陈之佛确实是一位具有世界性眼光和视野的一代文化巨人,不仅在20世纪上半期,即使在现在,也是不可多得的文化精英。”雅范虽未专攻工笔花鸟而选择乱针绣,但从小多受父亲影响教诲,在乱针绣之路上同样走着传承和创新的道路。乱针绣本身就是中国刺绣的创新,而乱针绣的发展又需要海峡两岸各家进行独具个人魅力的再度创造。近代发明而于现代光大的乱针绣,标志着刺绣从闺阁中走出来彻底解放——从实用绣、“闺阁绣”发展为纯供欣赏的艺术品。在创新技法上,除了针法的变化外,还能够求助于质材的变化,目前的创新有铺棉绣法、绕丝绣法、衬托绣法、留色绣法、虚实绣法、拼布法等等。中国的刺绣一步步走向了纯艺术化的道路,因此乱针绣也是中国刺绣纯艺术化的产物。 艺术上的使命感和迎难而上也是父女共通之处。自1931年起,陈之佛先生在教学之余挤出时间专攻工笔花鸟画,当时他已近不惑之年,在工艺美术上颇负盛名,毅然改变方向无疑需要巨大的勇气。自从文人画盛行以来,“逸笔草草”的作品风靡一时,工笔画家寥若晨星,面对明清以来中国花鸟画的颓废,他有心力挽颓风,振兴这一艺术。陈雅范也如此,重拾艺术也是到了她年近不惑,她说:“我是该专心于绘画,还是刺绣?由于当时从事绘画的人才太多,而近半世纪来刺绣的发展一直无法突破,没有创新,最后我选择了乱针刺绣,我下定决心,要在台湾将乱针绣发扬并引领到一个新的境界。”传统刺绣给人的印象是工细、平实、整齐,一般常见的如平针绣、双面绣等。而乱针绣给人的感觉是活泼自由,技法上打破旧有的排笔针法,绣者可以随自己的创意与技巧去表达。陈雅范打破常规,折冲东西,大胆地采用间色线法,运用“色彩学”类似色与补色原理,来增加绣面色阶的层次和丰富的色感,更突出乱针绣和其他刺绣的不同。在技法上,研发出绕丝、铺棉等方法,作品绣成之后极具立体感,色感强烈,线条优美,并可表现出渲染、虚实效果,与现代绘画艺术有异曲同工之妙,把乱针绣提升到“绣”“画”合一的艺术层面,突破了工艺的范畴。多元化的艺术创作已趋向于复合媒材的运作。乱针绣与油彩、水彩、水墨等画法结合,又可创作出新的作品。乱针绣技法与特色是“活用针线”,迷人处和困难度是对等的,不仅需用敏感的头脑,灵巧的双手,更少不了敏锐的观察力。虽然创作过程辛苦磨人,但最后得到的却是满心喜悦。刺绣在传统历史中渐渐发展成符合现代风味的艺术,这就是陈雅范以一生心力为之奋斗了五十年的乱针绣。
不知当时远隔大陆的陈雅范是否知道,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她的父亲陈之佛除了继续他的工笔画创作,又投入了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的抢救和指导工作。在他的多次呼吁下,江苏省成立了“苏州刺绣研究所”,亲自为苏绣画绣稿,《松龄鹤寿》《月雁》《石榴群鸡》等作品是其中的代表作。陈之佛集工艺工笔和教学于一身,他是三位一体的大师。而海峡彼岸的陈雅范在得闻父亲的噩耗后坚定了走苏绣奇葩乱针绣的道路,两岸音讯阻隔,这是冥冥之中的暗合和呼应吧?《松龄鹤寿》初稿是陈之佛1959年的力作,通幅笔法精奇,气势磅礴,是他生平罕见的巨制。28年后,为纪念乃父,陈嗣雪七秩之年以此为底稿飞针走线绣了四连屏巨作,工笔和写意的结合,运用创新技法——更为重要的是,又昭示了“嗣雪”的意义,此作正是长女嗣雪继承乃父尚美精神的物化。
陈之佛说过,他的第一职业是教书。当年广州美专的几十个学生紧随他的脚步,他走到哪里,他们跟到哪里,可见他为人师表的人格魅力。同样,在海峡彼岸,陈嗣雪嗣后做着继续雪翁尚美而甘苦的事业。1992年,陈嗣雪应邀在台中省立美术馆举行乱针绣推广展,由教育部主办暑期高中高职教师“乱针绣培训班”。2003年初,陈嗣雪在台北信义社区大学指导教授乱针绣,继而又在内湖社区大学教授,两地学员超过百人。陈嗣雪和蔼可亲,有教无类,社区大学的学员都非常喜欢“外婆”陈老师。
高尔泰在《广陵散》文中最后说,“从此乱针绝技,终于广陵散绝。”文章这么收尾,妙绝,但事实上乱针绣并未“广陵散”,传衣钵者虽不多也可谓不少,陈雅范就是其中一例。雅范有女,蔡文怡蔡文恂姐妹皆传其衣钵并致力于推广传习乱针绣。文怡从事传媒,退休后也习乱针,让人感叹非专业人士也绣出如此高难绣品,莫非是遗传效应?蔡文恂,台师大美术系毕业,原习水彩,为承母亲衣钵改学乱针绣,是雅范的学生又是她得力的助教。乱针绣,可写意空灵,可工笔写真,以绣代画也可绣画综合。绣画综合,以乱针刺绣绣出主体,再用丙烯(亚克力)画的方式绘出背景部分,不同媒质的相互运用产生浮雕立体效果,更显出乱针绣的层次感。然天不假年,清明时节我在运思作文之初突闻噩耗,之佛之后蔡文恂女士已于清明前夕在台不幸去世!天哪!天下哪有这种催稿的方式?孰可逆料孰可想象?让我的笔头为之怅惘郁闷失控,情何以堪!情何以堪!去年岁尾,她与姊文怡共同完成了母亲的一个遗愿,在母亲出生的地方,在外祖父陈之佛先生的老屋,展出一家三代绘画和乱针绣作品,并向陈之佛艺术馆捐赠作品。除了乱针绣,还展出了文恂女士较多数量和高质量的水彩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得到慈溪画界的一致首肯。她是一位热情爽朗不知疲倦的艺术家,我们自己老家人!浒山晓记弄是她的外婆家。然这竟是她最初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展览,不,我愿意看到她的遗作重回她的故里!向以为中国书法中国画是国粹,今日观之,苏绣乱针绣又何尝不是!